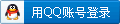一 个 人 的 时 光
文/ Cancan
一个人的时光
云朵不是投影山上
天空弯下腰嘻戏蜩蜋和螳螂
铃兰,牵牛和兔儿伞*
齐声摇晃着太阳
晚香玉,再不只是细语月亮
一个人的时光
你的模样,会是那样的安祥
明瞳映亮暮中的山岗
风儿传送着你的歌唱
她让石阶,紫藤和窗栏
当上只听命于你的花匠
一个人的时光
款目你笑靨的雪照绝潢
那是怎样的燕妬鶯惭,桃羞杏让
怎样粧见施嬙
和怎样地令人痴狂
不知别后你是否也曾这般孤寂彷徨
忆起那只选中了少年你我的龙舫
一个人的时光
思绪不需要精致的楼宇霓裳
那就由她干云翱翔
无羁,信马由缰
再次踏上那径遍洒鲜花的长廊
让欢欣镶上你钟爱的粉蔷 ——
在一个人的时光
拂去讬梦里的遍体鳞伤
-----
*:这三种花开放时铃兰低头,牵牛平放,兔儿伞朝天。< (诗中提到几种读者不太熟知的植物,方便阅读起见,附上它们的摄影图片)

兔儿伞
蜩蜋: 一种夏天鸣叫的青绿色叶蝉,又叫夏知了。款目:细数,罗列。)
-------------------
P.S. 附上这首诗发出之后诗风灵动的采采小妹写给我的英文小诗和两首回赠:
To Cancan
by 采采
Gentle leaves
Only in your hands
To take a mountain of green
Onto the hope of train
So i can tell the children
With my special love deepen
In unlimited darkness
Never lose original awareness
Gorgeous sunshine in my life
Like a beautiful bright wife
To bring what i cherish
Draw you a most honest wish
Oh, flower-like August
Rush to the sea in the east
注释:
1,登山时曾经见到一丛十来公分高的白色透明吊钟花一样的植物,急忙回身看看身旁是否有一个耶稣。后来在离家不远的山谷再次看见一样的透明鲜花,这次知道她们是真的大自然植物水晶兰(Cheilotheca, 鹿蹄草科)。再后面从网上又看到两种真实野生存在的透明花卉。
2,Flourishing 是近来西方兴起的新概念,大体可以翻译为盛多,繁茂精彩,跟古汉语里面的“采采”意思相通。因而题目里面精灵采采的英译采用Fairy Flourishing(F. F.)。
3,宇宙目前可以探测到的直径从过去的780亿光年扩大到接近一千亿光年,但是这只是天体物理学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范围,所以,可以说宇宙无边无际。对于这样存在着大量以冰为主的星球“丸子”的宇宙,推测想象宇宙中存在有透明的星星月亮,不算是异想天开。
4,從目前天文學家觀測彗星(約600多顆)所得的資料看,彗星的主要成份为有水,另有氮氣、氧氣、甲烷及山埃(Hydrogen Cyanide, HCN)等等。這些水分和氣體是以固態(即冰)的形式存在的。因此,美國天文學家Fred Whipple稱彗星的外号叫「髒雪球」(Dirty Snowball)。這些我们周围的「髒雪球」,都是源於太陽系邊緣處的奧爾特雲(Oort Cloud),那里“堆放”的是形成太陽系形成时的一些剩餘的物资。因為太阳引力的影響,這些多余天體偶爾便會向太陽系內通过扁椭圆的斜插轨道飛进来。
⬜
自然界的透明蝴蝶(Transparent Wing Butterflies)

水晶兰 Cheilotheca

自然界里面的透明花朵
一个人的时光,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安排,梭罗用它来思索人生和社会,因此,对于今天不那么会思索的人来说,去仔细阅读梭罗的思索是个不错的做法:
摘自梭罗《瓦尔登湖》一书后面的结束语
生了病的话,医生要明智地劝告你转移个地方,换换空气。谢天谢地,世界并不只限于这里。七叶树没有在新英格兰生长,这里也难得听到模仿鸟(琴鸟)。野鹅比起我们来更加国际化,它们在加拿大用早饭,在俄亥俄州吃中饭,夜间到南方的河湾上去修饰自己的羽毛。甚至野牛也相当地追随着时令节气,它在科罗拉多牧场上吃草,一直吃到黄石公园又有更绿更甜的草在等待它的时候。然而我们人却认为,如果拆掉栏杆或篱笆,在田园周围砌上石墙的话,我们的生活可就有了界墙,我们的命运方能安定。如果你被挑选为市镇的办事员,那你今夏就不能到火地岛去旅行,但你很可能到地狱的火里去。宇宙比我们看到的还要来得大呵。
然而我们应该更经常地像好奇的旅行家一样在船尾浏览周遭的风景,不要一面旅行,一面却像愚蠢的水手,只顾低头撕麻絮。其实地球的另一面也不过是和我们通信的人家。我们的旅行只是兜了一个大圈子,而医生开方子,也只能医治你的皮肤病。有人赶到南非洲去狩猎长颈鹿,实在他应该追逐的不是这种动物。你说一个人又有多久的时候追逐长颈鹿呢!猎取鹬鸟捉土拨鼠已算是罕有的游戏了,我认为枪击你自己会是更崇高的一项狩猎运动。——
“快把你的视线转向内心,
你将发现你心中有一千处
未曾发现的世界。那末去旅行,
成为家庭宇宙志的地理专家。”
非洲是什么意思,——西方又代表什么呢?在我们的内心的地图上,不就是一块等待探险之地吗?一旦将它发现,它还不是像海岸一样,是黑黑山林的吗?是否要我们一定要去尼罗河的河源,或尼日尔河,或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或我们这大陆上的西北走廊才算是探险呢?难道这些才是跟人类进行思索最有关系的条件吗?
弗兰克林爵士是否是这世上唯一失踪了的北极探险家,因此他的太太必须这样焦急地找寻他呢。格林奈尔先生是否知道他自己在什么地方?让你自己成为考察自己的江河海洋的门戈·派克、刘易士、克拉克和弗罗比秀之流吧;去勘探你自己的更高纬度去吧,——必要的话,船上装足了罐头肉,以维持你的生命,你还可以把空罐头堆得跟天空一样高,作为标志之用。发明罐头肉难道仅仅是为了保藏肉类吗?
不,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海峡,并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思想的流通。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主人,沙皇的帝国和这个领域一比较,只成了蕞尔小国,一个冰天雪地中的小疙瘩。然而有的人就不知道尊重自己,却奢谈爱国,而为了少数人的缘故,要大多数人当牺牲品。他们爱上他们将来要葬身的土地,却不理睬使他们的躯体活泼起来的精神。没有精神,爱国只是他们脑子里的空想。南大洋探险队是什么意思呢?那样的排场,那样的耗费,间接他说,那只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精神生活的世界中,虽然有的是海洋和大陆,其中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半岛和一个岛屿,然而他不去探这个险;他却坐在一只政府拨给他的大船中间,航行经过儿千里的寒冷、风暴和吃人生番之地,带着五百名水手和仆人来服侍他;他觉得这比在内心的海洋上探险,比在单独一个人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探险,倒是容易得多呢。
“Erret, et extremos alter scrutetur lberos。
Plus habet hic vitae, plus habet ille viae。”
“让他们去漂泊去考察异邦的澳大利亚人,
我从上帝得到的多,他们得到更多的路。”
周游全世界,跑到桑给巴尔去数老虎的多少,是不值得的。但没有更好的事情做,这甚至还是值得做的事情,也许你能找到“薛美斯的洞”,从那里你最后可以进入到你内心的深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黄金海岸、奴隶海岸,都面对着内心的海洋;可是从那里出发,都可以直航印度,却没有哪一条船敢开出港湾,远航到茫茫不见大陆的内心海洋上。尽管你学会了一切方言,习惯了一切风俗,尽管你比一切旅行家旅行得更远,适应了一切的气候和水土,连那斯芬克斯也给你气死撞碎在石上了,你还是要听从古代哲学家的一句话,“到你内心去探险。”这才用得到眼睛和脑子。只有败军之将和逃兵才能走上这个战场,只有懦夫和逃亡者才能在这里入伍。
现在就开始探险吧,走上那最远的西方之路,这样的探险并不停止在密西西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到古老的中国或日本去,这个探险一往无前,好像经过大地的一条切线,无论冬夏昼夜,日落月殁,都可以作灵魂的探险,一直探到最后地球消失之处。
据说米拉波到大路上试验了一次剪径的行为,“来测验一下,正式违抗社会最神圣的法律到底需要多少程度的决心”。他后来宣称“战场上的士兵所需要的勇气只有剪径强盗的一半”,——还说,“荣誉和宗教不能拦阻住一个审慎而坚定的决心。”而在这个世界上,米拉波总算是个男子汉了;可是这很无聊,即使他并不是无赖。一个比较清醒的人将发现自己“正式违抗”所谓“社会最神圣的法律”的次数是太多了,因为他服从一些更加神圣的法律,他不故意这样做,也已经测验了他自己的决心。其实他不必对社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只要保持原来的态度,仅仅服从他自己的法则,如果他能碰到一个公正的政府,他这样做是不会和它对抗的。
我离开森林,就如我进入森林,二者有同样好的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了。惊人的是我们很容易糊里糊涂习惯于一种生活,踏出一条自己的一定轨迹。在那儿住不到一星期,我的脚就踏出了一条小径,从门口一直通到湖滨;距今不觉五六年了,这小径依然还在。是的,我想是别人也走了这条小径了,所以它还在通行。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想人世的公路如何给践踏得尘埃蔽天,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何等深的车辙!我不愿坐在房舱里,宁肯站在世界的桅杆前与甲板上,因为从那里我更能看清群峰中的皓月。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
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想望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将要把一些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着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要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新解释,他将要拿到许可证,生活在事物的更高级的秩序中。他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去。
英国和美国提出了奇怪可笑的要求,要求你说话必须能被他们理解。人生和毒菌的生长都不是这样听命的。还以为这很重要,好像没有了他们便没有人来理解你了。好像大自然只赞成这样一种理解的能力,它养得活四足动物而并不能养活鸟雀,养活了走兽而养不活飞禽,轻声,别说话和站住的吆喝,好像成了最好的英文,连勃莱特也能懂得的。仿佛只有愚蠢倒能永保安全!我最担心的是我表达的还不够过火呢,我担心我的表达不能超过我自己的日常经验的狭隘范围,来适应我所肯定的真理!过火!这要看你处在什么境地。漂泊的水牛跑到另一个纬度去找新的牧场,并不比奶牛在喂奶时踢翻了铅桶,跳过了牛栏,奔到小牛身边去,来得更加过火。我希望在一些没有束缚的地方说话;像一个清醒的人跟另一些清醒的人那样他说话;我觉得,要给真正的表达奠立一个基础,我还不够过火呢。谁听到过一段音乐就害怕自己会永远说话说得过火呢?为了未来或为了可能的事物,我们应该生活得不太紧张,表面上不要外露,轮廓不妨暧昧而朦胧些,正如我们的影子,对着太阳也会显得不知不觉地汗流浃背的。我们的真实的语言易于蒸发掉,常使一些残余下来的语言变得不适用。它们的真实是时刻改变的;只有它的文字形式还保留着。表达我们的信心和虔诚的文字是很不确定的;它们只对于卓越的人才有意义,其芳馨如乳香。
为什么我们时常降低我们的智力到了愚笨的程度,而又去赞美它为常识?最平常的常识是睡着的人的意识,在他们打鼾 中表达出来的。有时我们把难得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归为一类,因为我们只能欣赏他们的三分之一的聪明。有人偶然起了一次早,就对黎明的红霞挑剔开了。我还听说过,“他们认为卡比尔的诗有四种不同的意义;幻觉、精神、智性和吠陀经典的通俗教义。”可是我们这里要是有人给一个作品做了一种以上的解释,大家就要纷纷责难了。英国努力防治土豆腐烂,难道就不 努力医治脑子腐烂?而后者实在是更普遍更危险的呢。
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变得更深奥了,可是,从我这些印张上找出来的致命缺点如果不比从这瓦尔登湖的冰上找出来更多的话,我就感觉到很骄做了。你看南方的冰商反对它的蓝色,仿佛那是泥浆,其实这是它纯洁的证明,他们反而看中了剑桥之水,那是白色的,但有一股草腥气。人们所爱好的纯洁是包裹着大地的雾,而不是上面那蓝色的太空。
有人嘀咕着,说我们美国人及一般近代人,和古人比较起来,甚至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比较起来,都不过是智力上的矮子罢了。这话什么意思?一只活着的狗总比一头死去的狮子好。难道一个人属于矮子一类便该上吊?为什么他不能做矮子中最长的一人。人人该管他自己的事情,努力于他的职责。
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要成功,而从事这样荒唐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伴侣们,那也许是因为他听的是另一种鼓声。让他踏着他听到的音乐节拍而走路,不管那拍子如何,或者在多远的地方。他应否像一株苹果树或橡树那样快地成熟,并不是重要的,他该不该把他的春天变作夏天?如果我们所要求的情况还不够条件,我们能用来代替的任何现实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不要在一个空虚的现实上撞破了船。我们是否要费力去在头顶上面建立一个蓝色玻璃的天空呢,虽然完成后我们还要凝望那遥远得多的真实的天空,把前者视作并未建立过的一样?
在柯洛城中,有一个艺术家,他追求完美。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一有时间的因素就不能成为完美的艺术作品,凡是完美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立刻到森林中去找木料,他已决定不用那不合式的材料,就在他寻找着,一根又一根地选不中意而抛掉的这个期间,他的朋友们逐渐地离开了他,因为他们工作到老了之后都死掉了,可是他一点也没老。他一心一意,坚定而又高度虔诚,这一切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永久的青春。因为他并不跟时间妥协,时间就站在一旁叹气,拿他没办法。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适用的材料,柯洛城已是古湮的废墟,后来他就坐在废墟上,剥一根树枝的皮。他还没有给它造出一个形状来,坎达哈朝代已经结束了。他用了手杖的尖头,在沙土上写下那个民族的最后一人的名字来,然后他又继续工作。当他磨光了手杖,卡尔伯已经不是北极星了;他还没有装上金箍和饰有宝石的杖头,梵天都已经睡醒过好几次。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些话呢?最后完成的时候,它突然辉耀无比,成了梵天所创造的世界中间最美丽的一件作品,他在创造手杖之中创造了一个新制度,一个美妙而比例适度的新世界;其间古代古城虽都逝去了,新的更光荣的时代和城市却已代之而兴起。而现在他看到刨花还依然新鲜地堆在他的脚下,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所谓时间的流逝只是过眼幻影,时间一点也没逝去,就像梵天脑中闪过的思想立刻就点燃了几人脑中的火绒一样。材料纯粹,他的艺术纯粹;结果怎能不神奇?
我们能给予物质的外貌,最后没有一个能像真理这样于我们有利。只有真理,永不破蔽。大体说来,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地方,而是在一个虚设的位置上。只因我们天性脆弱,我们假定了一类情况,并把自己放了进去,这就同时有了两种情况,我们要从中脱身就加倍地困难了。清醒的时候,我们只注意事实,注意实际的情况。你要说你要说的话,别说你该说的话呵。任何真理都比虚伪好。补锅匠汤姆·海德站在断头台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告诉裁缝们,”他说,“在缝第一针之前,不要忘记了在他们的线尾打一个结。”他的伴侣的祈祷被忘记了。
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面对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言咒骂它。它不像你那样坏。你最富的时候,倒是最穷。爱找缺点的人就是到天堂里也找得到缺点。尽管贫困,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你也还有愉快,高兴,光荣的时辰。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像射在富户人家窗上一样光亮,在那门前,积雪同在早春溶化。我只看到,一个安心的人,在那里也像在皇官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城镇中的穷人,我看,倒往往是过着最独立不羁的生活。也许因为他们很伟大,所以受之无愧。
大多数人以为他们是超然的,不靠城镇来支援他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往往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来对付生活,他们毫不是超脱的,毋宁是不体面的。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不要找新花样,无论是新朋友或新衣服,来麻烦你自己。找旧的;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在变。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
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焦虑求发展,不要屈服于玩弄你的影响;这些全是浪费。卑贱像黑暗,闪耀着极美的光。贫穷与卑贱的阴影围住了我们,“可是瞧啊!我们的眼界扩大了。”我们常常被提醒,即使赐给我们克洛索斯的巨富,我们的目的一定还是如此,我们的方法将依然故我。况且,你如果受尽了贫穷的限制,例如连书报都买不起了,那时你也不过是被限制于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经验之内了:你不能不跟那些可以产生最多的糖和最多淀粉的物质打交道。最接近骨头地方的生命最甜蜜。你不会去做无聊的事了。在上的人宽宏大度,不会使那在下的人有任何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我住在一个铅墙的角隅中,那里已倒人了一点钟铜的合金。常常在我正午休息的时候,一种混乱的叮叮之声从外面传到了我的耳鼓中。这是我同时代人的声音。我的邻居在告诉我他们同那些著名的绅士淑女的奇遇,在夜宴桌上,他们遇见的那一些贵族;我对这些,正如我对《每日时报》的内容,同样不发生兴趣。一般的趣味和谈话资料总是关于服装和礼貌,可是笨鹅总归是笨鹅,随便你怎么打扮它。他们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英国和印度,佐治亚州或马萨诸塞州的某某大人,全是短暂的、瞬息即逝的现象,我几乎要像马穆鲁克的省长一样从他们的庭院中逃走。
我愿我行我素,不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即使我可以跟这个宇宙的建筑大师携手共行,我也不愿,——我不愿生活在这个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十九世纪生活中,宁可或立或坐,沉思着,听任这十九世纪过去。人们在庆祝些什么呢?他们都参加了某个事业的筹备委员会,随时预备听人家演说。上帝只是今天的主席,韦勃斯特是他的演说家。那些强烈地合理地吸引我的事物,我爱衡量它们的分量,处理它们,向它们转移;——决不拉住磅秤的横杆,来减少重量,——不假设一个情况,而是按照这个情况的实际来行事;旅行在我能够旅行的唯一的路上,在那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我。我不会在奠定坚实基础以前先造拱门而自满自足。我们不要玩冒险的把戏。什么都得有个结实的基础。
我们读到过一个旅行家问一个孩子,他面前的这个沼泽有没有一个坚固的底。孩子说有的。可是,旅行家的马立刻就陷了下去,陷到肚带了,他对孩子说,“我听你说的是这个沼泽有一个坚固的底。”“是有啊,”后者回答,“可是你还没有到达它的一半深呢。”社会的泥泽和流沙也如此。要知道这一点,却非年老的孩子不可。也只有在很难得,很凑巧之中,所想的,所说的那一些事才是好的。我不愿做一个在只有板条和灰浆的墙中钉入一只钉子的人,要是这样做了,那到半夜里我还会睡不着觉。给我一个锤子,让我来摸一摸钉板条。不要依赖表面上涂着的灰浆。锤入一只钉子,让它真真实实地钉紧,那我半夜里醒来了想想都很满意呢,——这样的工作,便是你召唤了文艺女神来看看,也毫无愧色的。这样做上帝才会帮你的忙,也只有这样做你的忙他才帮。每一个锤入的钉子应该作为宇宙大机器中的一部分。你这才是在继续这一个工作。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坐在一张放满了山珍海味的食桌前,受到奉承的招待,可是那里没有真理和诚意;宴罢之后,从这冷淡的桌上归来,我饥饿难当。这种招待冷得像冰。我想不必再用冰来冰冻它们了,他们告诉我酒的年代和美名;可是我想到了一种更古,却又更新、更纯粹、更光荣的饮料,但他们没有,要买也买不到。式样,建筑,庭园和“娱乐”,在我看来,有等于无。我去访问一个国王,他吩咐我在客厅里等他,像一个好客的人。我邻居中有一个人住在树洞里。他的行为才真有王者之风。我要是去访问他,结果一定会好得多。
我们还要有多久坐在走廊中,实行这些无聊的陈规陋习,弄得任何工作都荒诞不堪,还要有多久呢?好像一个人,每天一早就要苦修,还雇了一个人来给他种土豆;到下午,抱着预先想好的善心出去实行基督教徒的温柔与爱心!请想想中国的自大和那种人类的凝滞的自满。这一世代庆幸自己为一个光荣传统的最后一代;而在波士顿、伦敦、巴黎、罗马,想想它们历史多么悠久,它们还在说它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多么进步而沾沾自喜。有的是哲学学会的记录,对于伟人公开的赞美文章!好一个亚当,在夸耀他自己的美德了。“是的,我们做了伟大的事业了,唱出了神圣的歌了,它们是不朽的,”——在我们能记得它们的时候,自然是不朽的罗。可是古代亚述的有学问的团体和他们的伟人,——请问现在何在?我们是何等年轻的哲学家和实验家啊!我的读者之中,还没有一个人生活过整个人生。这些也许只是在人类的春天的几个月里。即便我们患了七年才治好的癣疥,我们也并没有看见康科德受过的十六年蝗灾。我们只晓得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一张薄膜。大多数人没有深入过水下六英尺,也没有跳高到六英尺以上。我们不知在哪里。况且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们是沉睡的。可是我们却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在地球上建立了秩序。
真的,我们倒是很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我们是有志气的人!我站在林中,看这森林地上的松针之中,蠕蠕爬行着的一只昆虫,看到它企图避开我的视线,自己去藏起来,我便问我自己,为什么它有这样谦逊的思想,要藏起它的头避开我,而我,也许可以帮助它,可以给它这个族类若干可喜的消息,这时我禁不住想起我们更伟大的施恩者,大智慧者,他也在俯视着我们这些宛如虫豸的人。
新奇的事物正在无穷尽地注入这个世界来,而我们却忍受着不可思议的愚蠢。我只要提起,在最开明的国土上,我们还在听怎样的说教就够了。现在还有快乐啊,悲哀啊,这种字眼,但这些都只是用鼻音唱出的赞美诗的叠句,实际上我们所信仰的还是平庸而卑下的。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换换衣服就行了。据说大英帝国很大,很可敬,而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等强国。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潮起潮落,这浪潮可以把大英帝国像小木片一样浮起来,如果他有决心记住这个。谁知道下一次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十七年蝗灾?我所生活在内的那个世界的政府,并不像英国政府那样,不是在夜宴之后,喝喝美酒并谈谈说说就建立起来的。
我们身体内的生命像河中的水。它可以今年涨得高,高得空前,洪水涨上枯焦的高地;甚至这样的一年也可能是多事之年,把我们所有的麝鼠都淹死。我们生活的地方不一定总是干燥的土地。我看到远远地,在内陆就有些河岸,远在科学还没有记录它们的泛滥之前,就曾受过江河的冲激。
大家都听到过新英格兰传说的这个故事,有一只强壮而美丽的爬虫,它从一只古老的苹果木桌子的干燥的活动桌板中爬了出来,那桌于放在一个农夫的厨房中间已经六十年了,先是在康涅狄格州,后来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来,那颗卵还比六十年前更早几年,当苹果树还活着的时候就下在里面了,因为这是可以根据它外面的年轮判断的;好几个星期来,已经听到它在里面咬着了,它大约是受到一只钵头的热气才孵化的。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之后,谁能不感到增强了复活的信心与不朽的信心呢?这虫卵已经几个世代地埋在好几层的、一圈圈围住的木头中间,放在枯燥的社会生活之中,起先在青青的有生命的白木质之间,后来这东西渐渐成了一个风干得很好的坟墓了,——也许它已经咬了几年之久,使那坐在这欢宴的餐桌前的一家子听到声音惊惶失措,——谁知道何等美丽的、有翅膀的生命突然从社会中最不值钱的、人家送的家具中,一下子跳了出来,终于享受了它完美的生命的夏天!
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约纳森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可是时间尽管流逝,而黎明始终不来的那个明天,它具备着这样的特性。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
附旧文:
诗意是意识流
Virginia Woolf as a child. 儿时的伍尔芙
Member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in the Dreadnought Hoax
(Virginia Woolf is on the far left, 左一是Bloomsbury艺术家俱乐部里着男装的伍尔芙)
《THE MARK ON THE WALL 墙上的斑点》
.
.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要确定是在哪一天,就得回忆当时我看见了些什么。现在我记起了炉子里的火,一 片黄色的火光一动不动地照射在我的书页上;壁炉上圆形玻璃缸里插着三朵菊花。对了,一定是冬天,我们刚喝完茶,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吸烟,一仰头,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这个斑点打断了我这个幻觉,使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过去的幻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可能是在孩童时期产生的。墙上的斑点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
思绪是多么容易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像一群蚂蚁狂热地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又把它扔在那里…… 如果这斑点只是一只钉子留下的痕迹,那一定不是为了挂一幅油画,而是为了挂一幅小肖像画——一幅卷发上扑着白粉、脸上抹着脂粉、嘴唇像红石竹花的贵妇人肖像。它当然是一件赝品, 这所房子以前的房客只会选那一类的画—— 老房子得有老式画像来配它。他们就是这种人家—— 很有意思的人家,我常常想到他们,都是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因为谁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后来的遭遇了。据说,那家人搬出这所房子是因为他们想换一套别种式样的家具,他说着按他的想法,艺术品背后应该包含着思想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一下子分了手,这种情形就像坐火车一样,我们在火车里看见路旁郊外别墅里有个老太太正准备倒茶,有个年轻人正举起球拍打网球,火车一晃而过,我们就和老太太以及年轻人分了手,把他们抛在火车后面。
但是,我还是弄不清那个斑点到底是什么;我想,它不像是钉子留下的痕迹。它太大、太圆了。我本来可以站起来,但是,即使我站起身来瞧瞧它, 十之八九我也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一旦一件事发生以后,就没有人能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了。唉! 天哪,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 人类是多么无知!
那么来世呢?
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 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意像念头…… 莎士比亚……对啦,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行。这个人稳稳地坐在扶手椅里,凝视着炉火,就这样——一阵骤雨似的念头源源不断地从某个非常高的天国倾泻而下, 进入他的头脑。他把前额倚在自己的手上,于是人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张望——我们假设这个景象发生在夏天的傍晚——可是,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虚构是多么 沉闷啊! 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它也不完全是圆形的。我不敢肯定,不过它似乎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使我觉得如果我用手 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一个平滑的古冢,就像南部丘陵草原地带的那些古冢,据说,它们要不是坟墓,就是宿营地。在两者 之中,我倒宁愿它们是坟墓,我像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并且认为在散步结束时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定有一部书写到过它。一定有哪位古 物收藏家把这些白骨发掘出来,给它们起了名字……我想知道古物收藏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多半准是些退役的上校,领着一伙上了年纪的工人爬到这儿的顶上,检查 泥块和石头,和附近的牧师互相通信。牧师在早餐的时候拆开信件来看,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比较不同的箭镞,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这种 旅行对于牧师和他们的老伴都是一种愉快的职责,他们的老伴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那个关于营地或者坟墓的重大问题长期悬 而不决。而上校本人对于就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能否搜集到证据则感到愉快而达观。的确,他最后终于倾向于营地说。由于受到反对,他便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当 地会社的季度例会上宣读,恰好在这时他中风病倒,他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不是想到妻子和儿女,而是想到营地和箭镞,这个箭镞已经被收藏进当地博物馆的展柜,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的脚、一把伊利莎白时代的铁钉、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我真的 不知道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真的,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浮木。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把那两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 逐人了虚无的幻境。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 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我们想弄清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 的事物。它产生于一棵树,树木会生长,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长在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这些全是我们喜欢去想的事物——它们长着、 长着,长了许多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炎热的午后,母牛在树下挥动着尾巴;树木把小河点染得这样翠绿一片,让你觉得那只一头扎进水里去的雌红松鸡,应该带着绿色的羽毛冒出水面来。我喜欢去想那些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我还喜欢去想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 我喜欢想像那棵树本身的情景:首先是它自身木质的细密干燥的感觉,然后想像它感受到雷雨的摧残;接下去就感到树液缓慢地、舒畅地一滴滴流出来。
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话: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 什么新闻都没有。这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 ……然而不论怎么,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就那么趴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 是一只蜗牛。
The Mark on the Wall
Virginia Woolf (1917)
PERHAPS IT WAS the middle of January in the present year that I first looked up and saw the mark on the wall. In order to fix a date it is necessary to remember what one saw. So now I think of the fire; the steady film of yellow light upon the page of my book; the three chrysanthemums in the round glass bowl on the mantelpiece. Yes,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ter time, and we had just finished our tea, for I remember that I was smoking a cigarette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the mark on the wall for the first time. I looked up through the smoke of my cigarette and my eye lodged for a moment upon the burning coals, and that old fancy of the crimson flag flapping from the castle tower came into my mind, and I thought of the cavalcade of red knights riding up the side of the black rock. Rather to my relief the sight of the mark interrupted the fancy, for it is an old fancy, an automatic fancy, made as a child perhaps. The mark was a small round mark, black upon the white wall, about six or seven inches above the mantelpiece.
How readily our thoughts swarm upon a new object, lifting it a little way, as ants carry a blade of straw so feverishly, and then leave it…. If that mark was made by a nail, it can’t have been for a picture, it must have been for a miniature–the miniature of a lady with white powdered curls, powder-dusted cheeks, and lips like red carnations. A fraud of course, for the people who had this house before us would have chosen pictures in that way–an old picture for an old room. That is the sort of people they were–very interesting people, and I think of them so often, in such queer places, because one will never see them again, never know what happened next. They wanted to leave this house because they wanted to change their style of furniture, so he said, and he was in process of saying that in his opinion art should have ideas behind it when we were torn asunder, as one is torn from the old lady about to pour out tea and the young man about to hit the tennis ball in the back garden of the suburban villa as one rushes past in the train.
But as for that mark, I’m not sure about it; I don’t believe it was made by a nail after all; it’s too big, too round, for that. I might get up, but if I got up and looked at it, ten to one I shouldn’t be able to say for certain; because once a thing’s done, no one ever knows how it happened. Oh! dear me, the mystery of life; The inaccuracy of thought! The ignorance of humanity! To show how very little control of our possessions we have–what an accidental affair this living is after all our civilization–let me just count over a few of the things lost in one lifetime, beginning, for that seems always the most mysterious of losses–what cat would gnaw, what rat would nibble–three pale blue canisters of book-binding tools? Then there were the bird cages, the iron hoops, the steel skates, the Queen Anne coal-scuttle, the bagatelle board, the hand organ–all gone, and jewels, too. Opals and emeralds, they lie about the roots of turnips. What a scraping paring affair it is to be sure! The wonder is that I’ve any clothes on my back, that I sit surrounded by solid furniture at this moment. Why, if one wants to compare life to anything, one must liken it to being blown through the Tube at fifty miles an hour–landing at the other end without a single hairpin in one’s hair! Shot out at the feet of God entirely naked! Tumbling head over heels in the asphodel meadows like brown paper parcels pitched down a shoot in the post office! With one’s hair flying back like the tail of a race-horse. Yes, that seems to express the rapidity of life, the perpetual waste and repair; all so casual, all so haphazard….
But after life. The slow pulling down of thick green stalks so that the cup of the flower, as it turns over, deluges one with purple and red light. Why, after all, should one not be born there as one is born here, helpless, speechless, unable to focus one’s eyesight, groping at the roots of the grass, at the toes of the Giants? As for saying which are trees, and which are men and women, or whether there are such things, that one won’t be in a condition to do for fifty years or so. There will be nothing but spaces of light and dark, intersected by thick stalks, and rather higher up perhaps, rose-shaped blots of an indistinct colour–dim pinks and blues–which will, as time goes on, become more definite, become–I don’t know what….
And yet that mark on the wall is not a hole at all. It may even be caused by some round black substance, such as a small rose leaf, left over from the summer, and I, not being a very vigilant housekeeper–look at the dust on the mantelpiece, for example, the dust which, so they say, buried Troy three times over, only fragments of pots utterly refusing annihilation, as one can believe.
The tree outside the window taps very gently on the pane…. I want to think quietly, calmly, spaciously, never to be interrupted, never to have to rise from my chair, to slip easily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without any sense of hostility, or obstacle. I want to sink deeper and deeper, away from the surface, with its hard separate facts. To steady myself, let me catch hold of the first idea that passes…. Shakespeare…. Well, he will do as well as another. A man who sat himself solidly in an arm-chair, and looked into the fire, so–A shower of ideas fell perpetually from some very high Heaven down through his mind. He leant his forehead on his hand, and people, looking in through the open door,–for this scene is supposed to take place on a summer’s evening–But how dull this is, this historical fiction! It doesn’t interest me at all. I wish I could hit upon a pleasant track of thought, a track indirectly reflecting credit upon myself, for those are the pleasantest thoughts, and very frequent even in the minds of modest mouse-coloured people, who believe genuinely that they dislike to hear their own praises. They are not thoughts directly praising oneself; that is the beauty of them; they are thoughts like this:
“And then I came into the room. They were discussing botany. I said how I’d seen a flower growing on a dust heap on the site of an old house in Kingsway. The seed, I said, must have been sown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rst. What flowers grew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rst?” I asked–(but I don’t remember the answer). Tall flowers with purple tassels to them perhaps. And so it goes on. All the time I’m dressing up the figure of myself in my own mind, lovingly, stealthily, not openly adoring it, for if I did that, I should catch myself out, and stretch my hand at once for a book in self-protection. Indeed, it is curious how instinctively one protects the image of oneself from idolatry or any other handling that could make it ridiculous, or too unlike the original to be believed in any longer. Or is it not so very curious after all?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Suppose the looking glass smashes, the image disappears, and the romantic figure with the green of forest depths all about it is there no longer, but only that shell of a person which is seen by other people–what an airless, shallow, bald, prominent world it becomes! A world not to be lived in. As we face each other in omnibuses and underground railways we are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that accounts for the vagueness, the gleam of glassiness, in our eyes. And the novelists in future will realize more and m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reflections, for of course there is not one reflection but an almost infinite number; those are the depths they will explore, those the phantoms they will pursue, leaving the description of reality more and more out of their stories, taking a knowledge of it for granted, as the Greeks did and Shakespeare perhaps–but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very worthless. The military sound of the word is enough. It recalls leading articles, cabinet ministers–a whole class of things indeed which as a child one thought the thing itself, the standard thing, the real thing, from which one could not depart save at the risk of nameless damnation. Generalizations bring back somehow Sunday in London, Sunday afternoon walks, Sunday luncheons, and also ways of speaking of the dead, clothes, and habits–like the habit of sitting all together in one room until a certain hour, although nobody liked it. There was a rule for everything. The rule for tablecloths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was that they should be made of tapestry with little yellow compartments marked upon them, such as you may see in photographs of the carpets in the corridors of the royal palaces. Tablecloths of a different kind were not real tablecloths. How shocking, and yet how wonderful it was to discover that these real things, Sunday luncheons, Sunday walks, country houses, and tablecloths were not entirely real, were indeed half phantoms, and the damnation which visited the disbeliever in them was only a sense of illegitimate freedom. What now takes the place of those things I wonder, those real standard things? Men perhaps, should you be a woman; the masculine point of view which governs our lives, which sets the standard, which establishes Whitaker’s Table of Precedency, which has become, I suppose, since the war half a phantom to many men and women, which soon, one may hope, will be laughed into the dustbin where the phantoms go, the mahogany sideboards and the Landseer prints, Gods and Devils, Hell and so forth, leaving us all with an intoxicating sense of illegitimate freedom–if freedom exists….
In certain lights that mark on the wall seems actually to project from the wall. Nor is it entirely circular. I cannot be sure, but it seems to cast a perceptible shadow, suggesting that if I ran my finger down that strip of the wall it would, at a certain point, mount and descend a small tumulus, a smooth tumulus like those barrows on the South Downs which are, they say, either tombs or camps. Of the two I should prefer them to be tombs, desiring melancholy like most English people, and finding it natural at the end of a walk to think of the bones stretched beneath the turf…. There must be some book about it. Some antiquary must have dug up those bones and given them a name…. What sort of a man is an antiquary, I wonder? Retired Colonels for the most part, I daresay, leading parties of aged labourers to the top here, examining clods of earth and stone, and getting into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neighbouring clergy, which, being opened at breakfast time, gives them a feeling of importance, and the comparison of arrow-heads necessitates cross-country journeys to the county towns, an agreeable necessity both to them and to their elderly wives, who wish to make plum jam or to clean out the study, and have every reason for keeping that great question of the camp or the tomb in perpetual suspension, while the Colonel himself feels agreeably philosophic in accumulating evid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It is true that he does finally incline to believe in the camp; and, being opposed, indites a pamphlet which he is about to read at the quarterly meeting of the local society when a stroke lays him low, and his last conscious thoughts are not of wife or child, but of the camp and that arrowhead there, which is now in the case at the local museum, together with the foot of a Chinese murderess, a handful of Elizabethan nails, a great many Tudor clay , a piece of Roman pottery, and the wine-glass that Nelson drank out of–proving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No, no, nothing is proved, nothing is known. And if I were to get up at this very moment and ascertain that the mark on the wall is really–what shall we say?–the head of a gigantic old nail, driven in two hundred years ago, which has now, owing to the patient attrition of many generations of housemaids, revealed its head above the coat of paint, and is taking its first view of modern life in the sight of a white-walled fire-lit room, what should I gain?–Knowledge? Matter for further speculation? I can think sitting still as well as standing up. And what is knowledge? What are our learned men save the descendants of witches and hermits who crouched in caves and in woods brewing herbs, interrogating shrew-mice and writing down the language of the stars? And the less we honour them as our superstitions dwindle and our respect for beauty and health of mind increases…. Yes, one could imagine a very pleasant world. A quiet, spacious world, with the flowers so red and blue in the open fields. A world without professors or specialists or house-keepers with the profiles of policemen, a world which one could slice with one’s thought as a fish slices the water with his fin, grazing the stems of the water-lilies, hanging suspended over nests of white sea eggs…. How peaceful it is down here, rooted in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nd gazing up through the grey waters, with their sudden gleams of light, and their reflections–if it were not for Whitaker’s Almanack–if it were not for the Table of Precedency!
I must jump up and see for myself what that mark on the wall really is–a nail, a rose-leaf, a crack in the wood?
Here is nature once more at her old game of self-preservation. This train of thought, she perceives, is threatening mere waste of energy, even some collision with reality, for who will ever be able to lift a finger against Whitaker’s Table of Precedency?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s followed by the Lord High Chancellor; the Lord High Chancellor is followed by the Archbishop of York. Everybody follows somebody, such is the philosophy of Whitaker; and the great thing is to know who follows whom. Whitaker knows, and let that, so Nature counsels, comfort you, instead of enraging you; and if you can’t be comforted, if you must shatter this hour of peace, think of the mark on the wall.
I understand Nature’s game–her prompting to take action as a way of ending any thought that threatens to excite or to pain. Hence, I suppose, comes our slight contempt for men of action–men, we assume, who don’t think. Still, there’s no harm in putting a full stop to one’s disagreeable thoughts by looking at a mark on the wall.
Indeed, now that I have fixed my eyes upon it, I feel that I have grasped a plank in the sea; I feel a satisfying sense of reality which at once turns the two Archbishops and the Lord High Chancellor to the shadows of shades. Here is something definite, something real. Thus, waking from a midnight dream of horror, one hastily turns on the light and lies quiescent, worshipping the chest of drawers, worshipping solidity, worshipping reality, worshipping the impersonal world which is a proof of some existence other than ours. That is what one wants to be sure of…. Wood is a pleasant thing to think about. It comes from a tree; and trees grow, and we don’t know how they grow. For years and years they grow, withou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us, in meadows, in forests, and by the side of rivers–all things one likes to think about. The cows swish their tails beneath them on hot afternoons; they paint rivers so green that when a moorhen dives one expects to see its feathers all green when it comes up again. I like to think of the fish balanced against the stream like flags blown out; and of water-beetles slowly raising domes of mud upon the bed of the river. I like to think of the tree itself: first the close dry sensation of being wood; then the grinding of the storm; then the slow, delicious ooze of sap. I like to think of it, too, on winter’s nights standing in the empty field with all leaves close-furled, nothing tender exposed to the iron bullets of the moon, a naked mast upon an earth that goes tumbling, tumbling, all night long. The song of birds must sound very loud and strange in June; and how cold the feet of insects must feel upon it, as they make laborious progresses up the creases of the bark, or sun themselves upon the thin green awning of the leaves, and look straight in front of them with diamond-cut red eyes…. One by one the fibres snap beneath the immense cold pressure of the earth, then the last storm comes and, falling, the highest branches drive deep into the ground again. Even so, life isn’t done with; there are a million patient, watchful lives still for a tree, all over the world, in bedrooms, in ships, on the pavement, lining rooms, where men and women sit after tea, smoking cigarettes. It is full of peaceful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this tree. I should like to take each one separately–but something is getting in the way…. Where was I? What has it all been about? A tree? A river? The Downs? Whitaker’s Almanack? The fields of asphodel? I can’t remember a thing. Everything’s moving, falling, slipping, vanishing…. There is a vast upheaval of matter. Someone is standing over me and saying–
“I’m going out to buy a newspaper.”
“Yes?”
“Though it’s no good buying newspapers…. Nothing ever happens. Curse this war; God damn this war!… All the same, I don’t see why we should have a snail on our wall.”
Ah, the mark on the wall! It was a snail.
.
文/汤安
"意识流"这个概念,这在以新词泛滥,颠覆成语,戏说历史,假知识滥觞为时尚的今天,显得比较落后,意识流是一个大约拿破仑三世梦想复辟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期的古老词汇。但是,意识流不是随风而逝的东西,不是喇叭裤,迪斯科,滚石,披头士,大哥大,那样尽舍昼夜的东西,它是现代的,永恒的,如果刻意比较的话,意识流是每一首诗词中都隐藏着的诗意,意境。
哲学上的意识是人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是人知道自我和了解世界的途径。不论是怀疑还是证实,“意识”应该说更象是人类于“无意识”之中感觉自己的过程,老子的“吾不知谁之子,象帝(缔)之先”,孔子的“不舍昼夜”,庄周的梦蝶,分别说明了意识的感知象是推理加信念,而且它是连贯流动的。
因而,"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认识论的哲学起点,有疑问才产生思考,因此,这种意识是他的“普遍怀疑”论的终点。
然而意识受到有什么规则和动力的驱动?
法语不是一种容易含混的语言,"Je pense, donc je suis" 明确表示:"我思,故我在"。中文是不是更加丰富和具有意识流之"象"? 对了,易经里面的象是意识的经典例子,伏羲梦巨龟,周文王梦飞熊,箕子见纣王进餐用象箸而震惊逃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五柳先生归去来兮辞,曹孟德所说“老骥伏枥”,毛泽东接下去说的“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这些都是意识流做主角的诗意。
"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是认识论哲学,断句为与原意不同的中文"我思故,我在",就成了老庄孔孟,莎士比亚,梅特林克和古今意象派诗人脑海里的意识流状态下的诗意。
诗人文人先有意识流,再有提笔为文,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些就是对意识的疏浚成型,发其势,导其流。因此它的传递,也就能如苏轼所说“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无论如何,跟随意识流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回顾一遍,也许是最简捷的介绍意识流文学意境的方式。
1 威廉·詹姆斯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创造出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个词,用来表示意识的流动特性,这个名词是他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论述的一个概念,最初见于詹姆斯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詹姆斯意识流强调意识的动态性,联系性和流动发展特性,承认意识有它自身以外的客观对象存在,并认为意识对它有认识的功能。
詹姆斯说: “形容意识最自然的比喻就是‘河’或‘流’。此后,我们说到意识的时候,让我们把它称作思想的河流,或是意识流,或是主观生活之流。”
他感受到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因此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它能使感觉中的现在与过去无缝衔接,不可分割。这几乎与诗词里面的意境是一回事,从流动的画面里自然地裹携着诗意,而不是形容或者描述诗的内容。诗不可描述,不然比兴之类的也就不能代表诗的创作了。
他提出意识有五个特点:
1,意识是属于个人的。至于有没有一个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孤立而纯粹思想,我们无法加以确定,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经验。
2,意识是经常变化着的,没有任何一种状态一经过去之后能够再现并和以前的这种状态完全相同 (就跟人不可能再次进入一样的河水中一样,大脑中不可能出现两次完全一样的意识流)。
3,意识是连续不断的。即使一个人的意识在时间上中断后(例如进入睡梦后)仍可以前后连成一体。这里指意识的本身,而不是意识所涉及的内容在时间上的连续,因此,它不妨碍时间在意识流里面的跳跃。
4,意识有它自身以外的对象,它永远同这种对象打交道,具有认知的功能。
5,意识对其对象有选择性,它总是对它的对象的某些部分发生兴趣,而对其余部分则加以排除或拒绝。
詹姆斯所描述的意识的特性只是表面的,未触及意识的本质。对后两点的坚持让詹姆斯落入了对意识的唯心看法,并且走向纯经验论,因此不难走向自己的观念的反面,发展为怀疑论者,提出“意识存在吗?” 的疑问,让他的意识流学说转变为主观唯心论。意识二字不曾跳出人们的思维,但却改变着人们,甚至异化人类。
意识的变化是由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所引起的,并且这里也包括意识主体自己的心理活动的变化。“意识”(consciousness)的字面意思是能“注意”和“认识”事物的东西,原意包括“注意”和“认识”对象是人所能感受的环境,the state of being awake and aware of one's surroundings,因此,虽然不清楚具体的产生机制,人可以提升自己的意识(raise one's consciousness)。
然而,除了与物质实体对立存在之外,意识本身的定义和分类却无法明确。意识是一个不完整的、模糊的概念,意识无法形容。
约翰·希尔勒通俗地将其解释成:“(意识是)从无梦的睡眠醒来之后,除非再次入睡或进入无意识状态,否则是持续进行的知觉、感觉或觉察的状态”。[具体细分为许多分支概念,如"边缘意识"(对注意范围边缘的刺激物所获得的模糊不清的意识,包括"下意识"(在不注意或只略微注意的情形下所得到的意识);"潜意识"(潜隐在意识层面之下的感情、欲望、恐惧等复杂经验,自然受到意识的控制与压抑,而个人不自觉知);"前意识"(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一种意识层面,或者是以前贮存在长时记忆中的非调用信息)]。这可以说是“我思故我在”的支持论调。
今天的意识流文学是经过意识流和象征主义文学大家提炼发展之后的辉煌产物:
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在《追憶似水年華》裡,描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貴族的沒落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普鲁斯特仅仅借助不由自主的回忆,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重现在读者眼前,就使时间在艺术中以永存:沙龙、戏院、海滨以及文人雅士、倩女俊男的君子好求式的生活,20世纪初巴黎浪漫的随之一一展现。而在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Á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里,作者重现20世纪初巴黎风华的非凡功力,"令任何风格都黯然失色!"。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
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意识流作家中成就最高的女性。代表作品《达洛维夫人》、《海浪》、《到灯塔去》和《墙上的斑点》。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诺贝尔文学奖意识流文学大家,代表作是一系列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小说,包括15个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最优秀的意识流作品。书名取自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著名台词,福克纳的著名意识流小说还包括《我弥留之际》,等等,等等。
2 詹姆斯.乔伊斯
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更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前意识。
“意识流”一词作为心理学词汇,是在威廉·詹姆斯之后,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绵延论”强调生命冲动的连绵性、多变性。他的关于“心理时间”与“空间时间”的区分、关于直觉的重要性以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结构和梦与艺术关系的理论,都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从此,"意识流文学"带来了现代主义文学里面的重要分支。
意识流小说家主张让人物主观感受到的“真实”客观地、自发地再现于纸面上,反对传统小说出面介绍人物的身世籍贯、外界环境、间或挺身而出评头论足的写法,要求作者“退出小说”。这个主张最初是由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提出的,后来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论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 。跟庞德类似,对人格的异化使艾略特随后走入理想幻灭和宗教救赎,虽然"符合"了战后六十年代人们的颓废特征,但似乎也因此离开了意识流文体,进入空幻,这种思潮随着他的获奖而泛滥实际上带来了战后“垮掉的一代”。
如何才能运用或者算是运用了意识流文体?
意识流文学的大家和代表人物乔伊斯是把消灭了作者人格的戏剧看作最高的美学形式,并力图在小说中达到这一目标。
运用意识流文体詹姆斯.乔伊斯给出了最好的事例,他认为作品是与外界事物绝缘的独立自足的有机结构。作为现成的艺术品,它不仅与社会、历史无关,甚至与作者本人也无关。因为社会历史因素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创作的素材,它们进入作品以后就被“艺术化”、“形式化”了,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文学和艺术的意识不是机械孤立和静止的,因而,只有当无尽的意识流动形成艺术感染和风格时,时空中的不断流动成了意识的活力和发展体现,具体的影像反而成为絷拌意识运动的累赘,因而,就象“写意中国画”一样,用笔不求工细,而是注重神态气韵的连贯和挥洒感染,通过简练放纵的笔致表现出意态神思和无限逸韵,“禀逸韵於天陶,含冲气於特秀” (晋 庾亮 《翟徵君赞》)。
然而,与人们所以为的天马行空荒诞不羁相反,意识流尤其需要其深厚的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与思考的基础,才能上接天赋下及地理,达到"含冲气於特秀"。意识流文学的每一篇经典巨作无不精雕细凿般充满着细碎精致而又贴切的描绘和比喻,活生生的"生活体验"也许可以说是深刻意识和意识流得以体现出来的源泉。
乔伊斯本人一生大部分时光都远离故土爱尔兰,但他象叶芝和其他知名爱尔兰艺术家一样(类似的还有诗人彭斯,拜伦,歌德,莎士比亚和契克夫),对祖国刻骨铭心的挚爱和早年在祖国的生活经历一直对他的创作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将他的思考和意识深深根植进爱尔兰这块无可撼动的故土之中,独具创作慧眼的乔伊斯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绝大部分作品都以内心中遥望故乡爱尔兰的浓厚意识做为背景和主题,让他的小说根植于早年在都柏林的生活,里面充满着包括他的家庭、朋友、敌人、中学和大学的岁月-----读过《尤利西斯》的人无不感染其中在对话和谈吐里面所充满着的老牌经典学院的人杰地灵和璀璨知识之光。这对于急着变化,异化,化的中国三流浮躁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之类是一种讽刺,尤其讥讽的是后者没有意识的诗意,境界庸俗,形神躲闪亏虚。
正是如此,意识流之外的深厚情感,哲学和生活经历成就了乔伊斯做为意识流大家如日中天的名望和作品无限的感染力,他被誉为"现代英语文学中将国际化因素和乡土化情节结合最好的人"。
这样的收获,恐怕同样会让今天充斥在"北京798"和莫斯科广场的一些所谓象征主义艺术(意识流的学派名称)的"行为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们大为不堪。
追求虚无的失败者坠入的是巴顿将军所喜欢讥讽的那些错过了辉煌的世界大战而只能对着孙儿们"回忆自己在田纳西铲牛粪的人生"的宿命。------有趣的是,巴顿将军所秉承的那句刻在他跟巴顿夫人的戒子中的缩写"在没有人的时候,上帝注释着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意识流的意境特色。
3 马赛尔·普鲁斯特, 弗吉尼亚·伍尔芙
介绍意识流作品如果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寻找失去的时间》)( Marcel Proust)那样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安静理智地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进行分析追索,在无人倾听的情况下获得“内心分析”,而不是独白,更容易形成以理性为指引和合乎逻辑规则的优美动人推理,并说明意识流不是任由意识的自然流动。那也许比啃《尤利西斯》更容易获得意识的逻辑感觉而少一些"眩晕"。[特别推荐:最近网上的一篇优美分析介绍文章"思羽:《追忆似水年华》之随想"]
然而,无论真正在意意识流与否,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于"墙上印迹"那样油然而起的意识流感觉,------通过一个生活中墙上,物体或者天空地面的印迹,连通到内心的图像意识,进而变换普通的平面印渍为内心和意识中流动起来的人物跟图像。
一个印迹,它的前生和下一步的是什么?思维由此流动开来 ------自由联想,时空转换,蒙太奇,色彩化,历史空间化,诗化,音乐化,以及它们的整合,到最后,先前那个印迹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导出的意境。
也许就跟美国诗坛领袖佛洛斯特对诗的描述一样,把这些意识的河流融汇进儿时的记忆,故乡的空气,家,国,情和爱恨就是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电影。启功先生说"这说诗,实际只是说了“半辈子,梦, 心,泪,热,早已知道”几个意思,是诗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顾。",应该说也是佛洛斯特的主旨,都有意识流的意味。
当然意识流也可以什么文体都不属于,只在内心思想活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象布莱克默小说《罗娜.邓恩》里面走过曦阳升起的山谷,获得爱和人生的清晰启示的乔.瑞德一样,终于将自己跟英国的命运和历史发展融汇在一起。
也许因为限于译文的篇幅,中国最突出的意识流介绍作品来自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尤其是成为中学教材的这位被誉为英国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的著名女作家的经典意识流小说 《THE MARK ON THE WALL 墙上的斑点》。
伍尔芙的母亲是位绝色佳人,曾为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爱德华·波恩 – 琼斯(Edward Burne-Jones)担任模特。伍尔芙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是当时显赫的贵族,编辑,文学评论家及传记作者。这些带来了伍尔芙的勇敢敏锐,在世界动荡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一个女子之力成为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代表者。
她提倡女权主义,文学创作上强调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不要机械地描写现实的生活,这一点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在英国文坛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格完全背道而驰,象李清照撰写词论一样,她大胆地把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这一类当时如日中天的一流作家称做"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虽然写得很成功,但是并没有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她比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等具有深刻思考分析功力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人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她最推崇的作家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伍尔芙把乔伊斯的创作称为"精神主义",伍尔芙的创作就是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完成的。
《墙上的斑点》是她第一篇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作者描述自己看到墙上的斑点,以此展开回忆和无数的联想,产生一系列幻觉和遐想,令人感叹生命象意识流那样充满着偶然性。
意识流先驱人物亨利·詹姆斯说:“针和线分离就不能缝衣,内容和形式割裂即不成其为艺术品。” 也许你能认为《墙上的斑点》就是这样一篇内容与形式难以区分,内容即形式,形式也就是内容的作品。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德是同时受到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所推崇的思想家,他的名言:『艺术是我,科学只是我们』(Art is I, science is we. —–Claude Bernard),说到底,文学创作就是在深厚的生活观察积累基础上的情感联想和抒发,是作者头脑中绚丽的情感和意识的书面流淌,是象诗歌那样的意境展示。
——
陌上花
文/Cancan
蕾,温绚,
光,晨曦。
雨,空寂,
土,无垠
意识流总是跟事物的倒影分不开,这也许是意识流的器外特性。



伍尔芙的母亲 Edward Burne-Jones 画中模特
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剑桥大学毕业生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伍尔芙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代表者。

诗友 秋竹声
信是人生意识流,
随情泼墨换春秋。
江山一卷丹青梦,
不到醒时何得休?
In my humble opinion, the mark on the wall is actually a pigment of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though. You can identify any object as something triggering off a creative process, if your mind is fertile enough. Any approach can get you a masterpiece, if you are a master to start with. Pure and simple.
诗友 璇月舞
【七绝】
一
精神世界玄关隐,
思想意识占主流。
浩荡奔腾终宇宙,
无中生有找源头。
二
天河瀚瀚夜奔流,
月上穹巅叶送秋。
巨变源头谁可溯,
星云之外始无休。
(翻译来自网上,依据原文上下的联系,对一些细节略有改动)
http://www.motie.com/s/app/notes/416/note/1919
.
.
为了证明我们对自己的私有物品是多么无法加以控制——和我们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啊——我只要列举少数几件我们一生中遗失的物件就够了。就从那三只装着订书工具的浅蓝色罐子说起吧,这永远是遗失的东西当中丢失得最神秘的几件——哪只猫会去咬它们,哪只老鼠会去啃它们呢?
再数下去,还有那 几个鸟笼子、铁裙箍、钢滑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弹子戏球台、手摇风琴——全都丢失了,还有一些珠宝,也遗失了。有乳白宝石、绿宝石,它们都散失在芜 菁的根部旁边。它们是花了多少心血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啊!
此刻我四周全是挺有分量的家具,身上还穿着几件衣服,简直是奇迹。要是拿什么来和生活相比的话, 就只能比做一个人以一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被射出地下铁道,从地道口出来的时候头发上一根发针也不剩。光着身子被射到上帝脚下! 头朝下脚朝天地摔倒在开满水仙花的草原上,就像一捆捆棕色纸袋被扔进邮局的输物管道一样!头发飞扬,就像一匹赛马会上跑马的尾巴。对了,这些比拟可以表达生活的飞快速度,表达那永不 休止的消耗和修理;一切都那么偶然,那么碰巧。
.
粗大的绿色茎条慢慢地被拉得弯曲下来,杯盏形的花倾覆了,它那紫色和红色的光芒笼罩着人们。人到底为什么要投生在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会行动、不会说话、无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脚下,在巨人的脚趾间摸索呢?
至于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或者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东西,人们再过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别的什么都不会有,只有充塞着光亮和黑暗的空间,中间隔着一条条粗大的茎干,也许在更高处还有一些色彩不很清晰的——淡淡的粉红色 或蓝色的——玫瑰花形状的斑块,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会越来越清楚、越——我也不知道怎样……可是墙上的斑点不是一个小孔。它很可能是什么暗黑色的圆形物 体,比如说,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造成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警惕心很高的管家——只要瞧瞧壁炉上的尘土就知道了,据说就是这样的尘土把特洛伊城严严地埋了三层,只有一些罐子的碎片是它们没法完全掩盖的,这一点完全能叫人相信。
.
我希望能碰上一条使人愉快的思路,同时这条思路也能间接地给我增添几分光彩,这样的想法是最令人愉快的。连那些真诚地相 信自己不爱听别人赞扬的谦虚而灰色的人们头脑里,也经常会产生这种想法。它们不是直接恭维自己,妙就妙在这里。
这些想法是这样的:“于是我走进屋子。他们在谈植物学。我说我曾经看见金斯威一座老房子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我说那粒花籽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种下的。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人们种些什么 花呢?” 我问道—— (但是我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也许是高大的、带着紫色花穗的花(指紫藤,通常代表年代感和厚重历时) 吧。
于是就这样想下去。同时,我一直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因为,我如果当真公开地这么干了,就会马上被自己抓住,我就会马上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掩盖自己。说来也真奇 怪,人们总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形象,不让偶像崇拜或是什么别的处理方式使它显得可笑,或者使它变得和原型太不相像以至于人们不相信它。
但是,这个事实也可 能并不那么奇怪? 这问题极其重要。假定镜子打碎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人的外壳 ——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浮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当我们面对面坐在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道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照镜 子;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眼神都那么呆滞而朦胧。
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认为这类知识是天生具有的。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或许莎士比亚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种概括毫无价值。只要听听概括这个词的音调就够了。它使人想起社论,想起内阁大臣—— 想起一整套事物,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认为这些事物是正统,是标准的、真正的事物, 人人都必须遵循,否则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
提起概括,不知怎么使人想起伦敦的星期日,星期日午后的散步,星期日的午餐,也使人想起已经去世的人的 说话方式,衣着打扮、习惯——例如大家一起坐在一间屋子里直到某一个钟点的习惯,尽管谁都不喜欢这么做。每件事都有一定的规矩。
在那个特定时期,桌布的规 矩就是一定要用花毯做成,上面印着黄色的小方格子,就像你在照片里看见的皇宫走廊里铺的地毯那样。另外一种花样的桌布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当我们发现这些 真实的事物、星期天的午餐、星期天的散步、庄园宅第和桌布等并不全是真实的,确实带着些幻影的味道,而不相信它们的人所得到的处罚只不过是一种非法的自由 感时,事情是多么使人惊奇,又是多么奇妙啊!我奇怪现在到底是什么代替了它们,代替了那些真正的、标准的东西? 也许是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男性的观 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 注释:*惠特克(1820--1895) ,英国出版商,创办过《书商》杂志,于1868年开始编纂惠特克年鉴)的尊卑序列表。
据我猜想,大战后它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已经带上幻影的味道,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像幻影、红木碗橱、兰西尔版画、上帝、魔 鬼和地狱之类东西一样遭到讥笑,被送进垃圾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 如果真存在自由的话……
.
不,不,我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现。假如我在此时此刻站起身来,弄明白墙上的斑点果真是——我们怎么说不好呢?——一枚巨 大的旧钉子的钉头,钉进墙里已经有两百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的擦拭,钉子的顶端得以露出到油漆外面,正在一间墙壁雪白、炉火熊熊的房间里 第一次看见现代的生活,我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知识吗?还是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题材? 不论是静坐着还是站起来我都一样能思考。
什么是知识? 我们的学者不 过是那些蹲在洞穴和森林里熬药草、盘问地老鼠或记载星辰的语言的巫婆和隐士们的后代,要不,他们还能是什么呢?我们的迷信逐渐消失,我们对美和健康的思想 越来越尊重,我们也就不那么崇敬他们了……是的,人们能够想像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宁而广阔,旷野里盛开着鲜红的和湛蓝的花朵。这个世界里没 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轻轻地掠过荷花的梗条,在装满白色海鸟卵的鸟窠上空盘旋……在世界的中心扎下根,透过灰黯的海水和水里瞬间的闪光以及倒影向上看去,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我 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一枚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 大自然又在这里玩弄她保存自己的老把戏了。她认为这条思路至 多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精力,或许会和现实发生一点冲突,因为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 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惠特克是知道的。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是应该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我懂得大自然耍的是什么把戏——她在暗中怂恿我们采取行动 以便结束那些容易令人兴奋或痛苦的思想。我想,正因如此,我们对实干家总不免稍有一点轻视—— 我们认为这类人不爱思索。不过,我们也不妨注视墙上的斑点,来打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
.
我还喜欢去 想这棵树怎样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树叶紧紧地合拢起来,对着月亮射出的铁弹,什么弱点也不暴露,像一根空荡荡的桅杆竖立在整夜不停地滚动 着的大地上。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拆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篷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 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到多么寒冷啊……大地的寒气凛冽逼人,压得树木的纤维一根根地断裂开来。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 的枝条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 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在喝过茶以后就坐在这间屋里抽烟。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我很愿意挨个儿去思索它们 ——可是遇到了阻碍……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 盛开水仙花的原野?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啦。一 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
.
.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
.
.
..
.
.
----
.
.
P.S.
1, "秋墙霜叶" 和"海草画" ,来自朋友/诗友叶子女士的摄影作品
2,"意识流"通常也是象征主义和后现代艺术作品和音乐的重要内涵 (反过来,意识流小说家为了加强象征性的效果,借鉴的是诗歌和音乐的写意手段,将读者的意会扩展成为作品意境的组成部分):

.
.
.

.
.
补上一个一直思考的问题作为结语
意识流在艺术领域里的发展也许最终可以成为象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论辩证法(Grand Unified Dialectics),和未来物理学中整合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的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ies,GUTs),用单一场论就可以允许所有种类的基本相互作用之间的基本粒子,在同一原则之下可以解释他们之间关系的物理理论)那样的艺术统一理论。所有的艺术,尤其是诗歌,音乐,绘画,最终都是通过意识流的整合,意境的升华和展示而为作者和读者所感受。
.